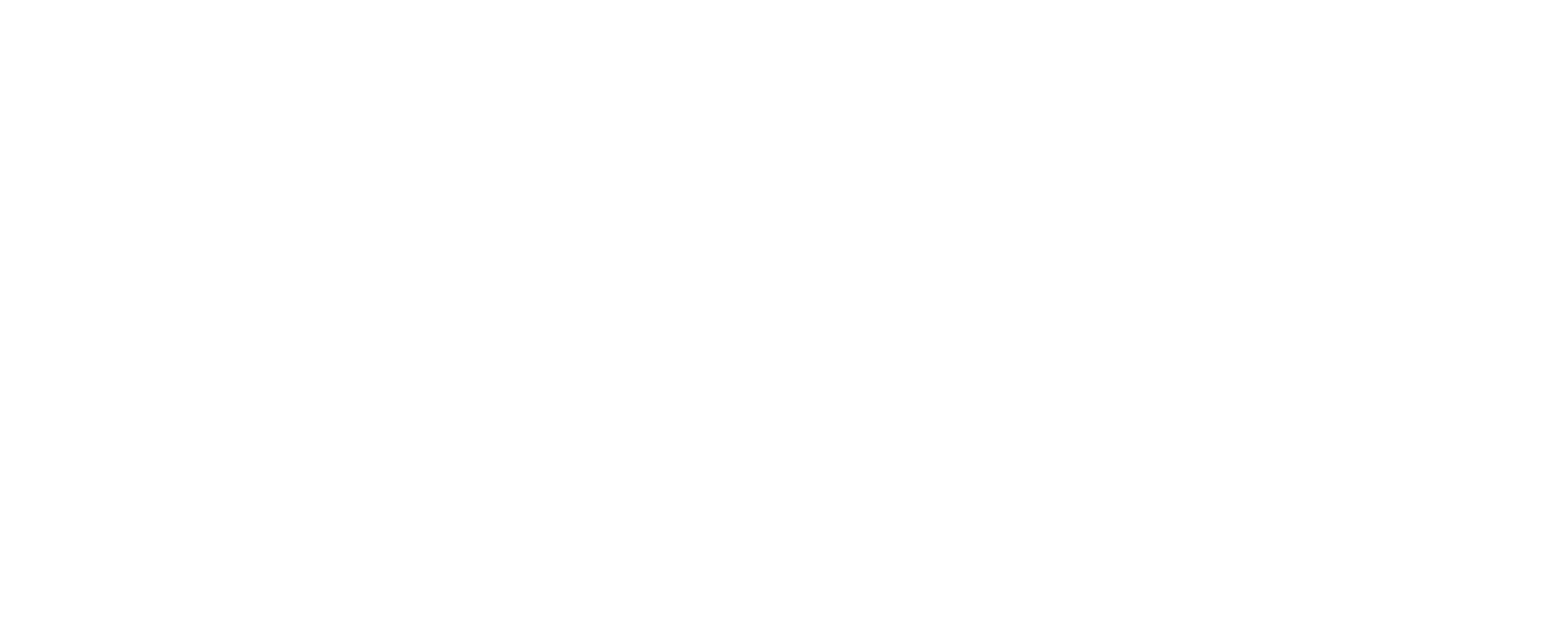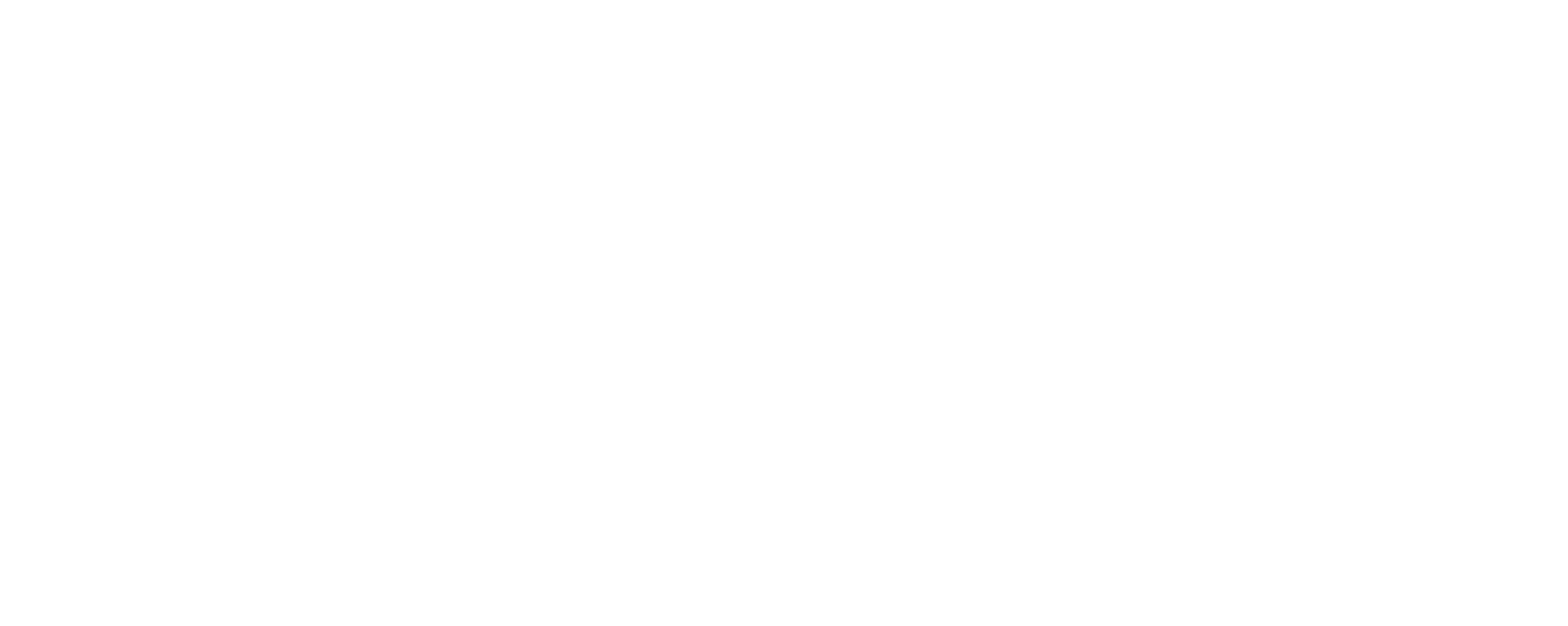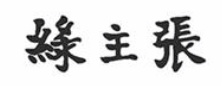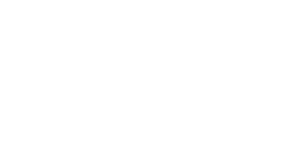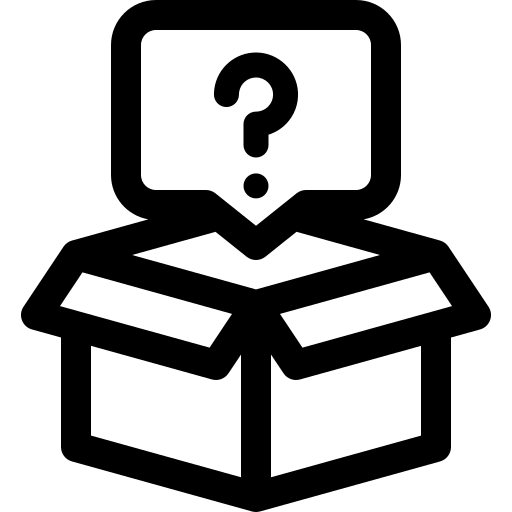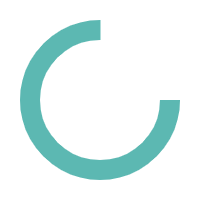人生最後旅程的種種:病中照顧的支持
2013-03-05・愛森林 從日常用紙開始
文。圖/楊佳羚
民間機構的居家伴陪員資訊。
在之前專欄中,我談到了媽媽病中身為家屬的我們的一些心情轉折。從那些分享中可以發現,照顧生病的家人,除了體力勞累,還有沉重的情緒負荷。這時,只靠家人的分擔是不足的。
居家陪伴員的協助
在媽媽生病最後幾個月,因為她長年來的失眠問題無法用安眠藥得到解決,所以常常是在晚餐後小睡幾小時,再來就清醒到天明。當她睡不著時,就會一直想起床上廁所,也有好幾次不小心跌倒。因此,爸爸常在一整天的照顧之後,半夜又得醒著陪媽媽一整夜。而我往往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出現,對於照顧媽媽其實沒分擔到什麼責任。再加上有時我實在害怕看到媽媽的疼痛,而有些逃避。面對這些,我想:該是找個人來幫忙的時候了。
當時立刻想到了彭婉如基金會的居家陪伴員─婉如基金會長年來投注於社區照顧議題,除了參與社區自治幼兒園、保姆系統的經營,也培訓了家事服務員與居家陪伴員,而後兩者,正是瑞典居家服務員的工作。在瑞典,是由市政府評估老人或病人的狀況,安排居家服務員幫忙購物、打掃,或是協助老病者洗澡、更衣、進食或在家醫療照護。如同我在媽媽過世前寫的「老人國也可以是幸福國」所提到的,台灣因為不公平的稅收制度及依職業區分的保險制度,使得台灣難以像瑞典一樣,由市政府聘雇這些照顧工作者。因此,婉如基金會採用的是另一個模式─她們以非營利的精神來建立社區式的照顧服務工作。也就是說,和一般人力派遣公司或營利的照顧機構不同的是基金會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壓縮照顧者的人事經費,以期讓這些照顧者得到合理的待遇。同時,又要建立一套制度,使得這些照顧工作者能得到基本的工作福利與保障,又能維持照顧工作者的服務品質。而這個制度就有賴我們這些雇主的互助捐款(如同雇主提撥的概念)、社區照顧服務人員工會與協會的建立、再加上基金會投注的資源。
當我向婉如基金會提出申請時,督導問了我一些關於媽媽的基本狀況。我特別強調,媽媽是很難取悅的病人,又沒有什麼嗜好,所以居陪員一定要本身很開朗才行。在居陪員來的五個半天中,當我有課無法陪媽媽去做放射治療時,就由她陪伴媽媽。媽媽有時在外人面前會比較配合,所以當媽媽吃膩了爸爸煮的東西,有時就由她來煮些新口味給媽媽嚐鮮。有時媽媽從醫院放療回來就累了,居陪員就趁媽媽休息時,幫忙按摩、換洗床單或衣服、或陪爸爸聊天。她對爸爸的稱讚、給媽媽的鼓勵,改善了當時緊繃的家庭氣氛。
社區照顧體系的建制
在之前專欄我也提到,台灣十年的長照計畫,仍使長期照護系統長不出來;目前所草擬的長照法,充其量只是「長期照顧機構管理辦法」,政府仍是以殘補式的福利思維在構思長期照顧,只用管理主義來讓長期照顧機構不出事、以極少的補助來提供居家服務、不足的則用不斷開放外籍社福移工的方式來解決。
最近關於年金制度的改革吵得沸沸揚揚,但仔細看政府所提的政策,仍欠缺全盤的思考。其實,目前台灣已經有普及式的健保,如果能以普及式的國民年金為基礎,再加上與所得相關的附加年金與工作保險,就能取代現在疊床架屋的普及式保險加上各個職業分流的職業保險,並且能達到公平正義的理想。也就是說,在這種普及式的保險制度底下, 所有人都享有一樣的福利(如育嬰、生病、職災或退休),而所拿到的現金津貼或給付,則是與其薪資相關, 但設有上下限, 這樣不但可以滿足中產階級的要求(因為薪水較高時所領的錢也比較高),又不至於將大部分的國家資源做逆向分配(如現今許多對大企業與有錢人的免稅、退稅、及獨厚軍公教的福利),同時還讓中下階層的人不需要透過層層的資產調查(以證明自己「夠慘」、「夠窮」)即可得到基本福利、不用在得到微薄福利時還得被污名化為「無所事事的米蟲」。也唯有這樣的福利制度,才不會造成不同職業之間的分化,以及如現今台灣社會所看到的階級對立。
而且,當國家社福資源不再以支撐軍公教福利為主時,才有足夠的錢來建立社區式的照顧體系,同時,也讓這種社區式的照顧體系,不但讓老病幼被照顧、讓之前因為照顧工作而被綁在家裡的女性能從事有薪水的工作,同時也創造了在地的就業機會。如果我們政府能有這樣的整體規劃, 就不會像現在被各方批評了。
當我們參訪瑞典老人照顧體系時,聽到「瑞典老人照顧仍有七成為家人承擔」時覺得驚訝不已。然而,當我自己經歷了媽媽的生病,才發現是真的─因為照顧老人的常常是老伴;而瑞典因為平均壽命長,照顧老人的除了老伴還有年屆退休的兒女。如果瑞典社會做了那麼完善的老人照顧體系,家人仍得負擔七成;那麼,我們台灣的家屬們,不就攬了一二○%的責任在身上嗎?面對這樣的議題,我們的政府還能坐視不管嗎?(作者:高師大性別教育所助理教授,著有《台灣女生 瑞典樂活》)

因照顧母親而請照顧假的瑞典女性。
原刊登於《綠主張》月刊2013年3月1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