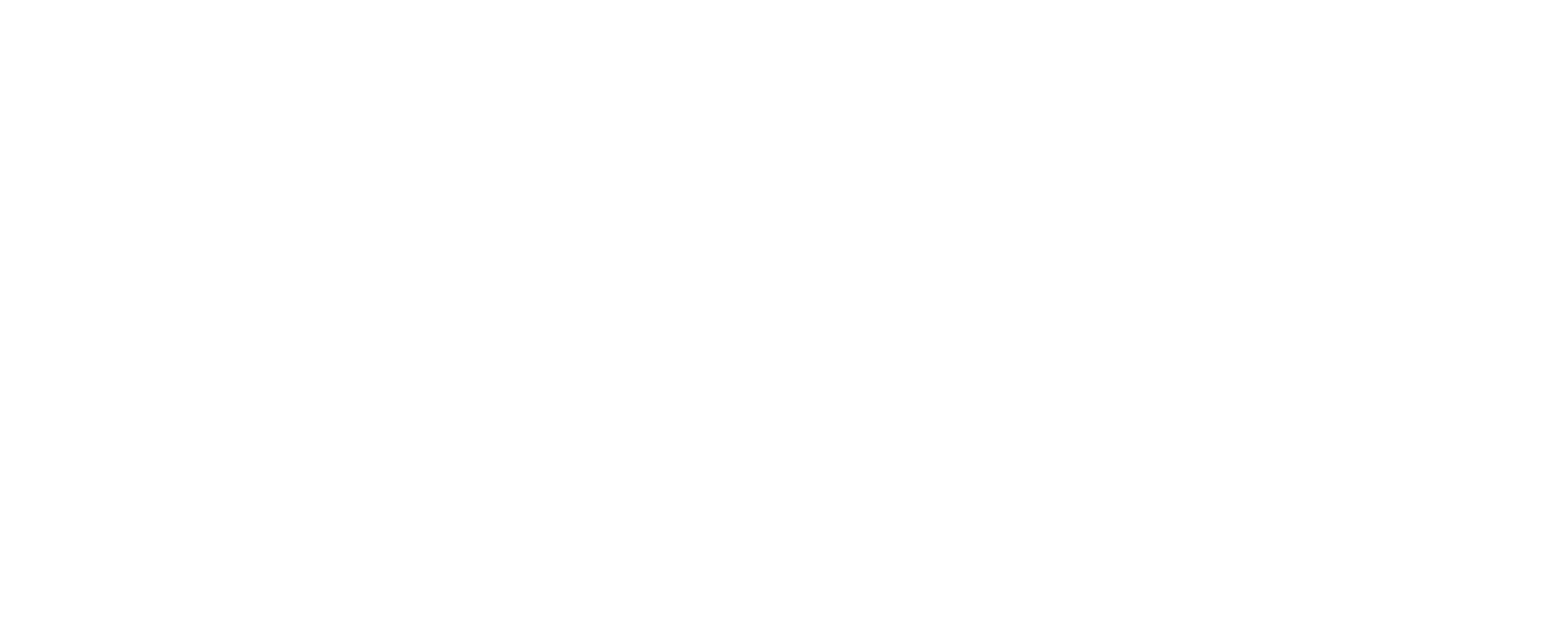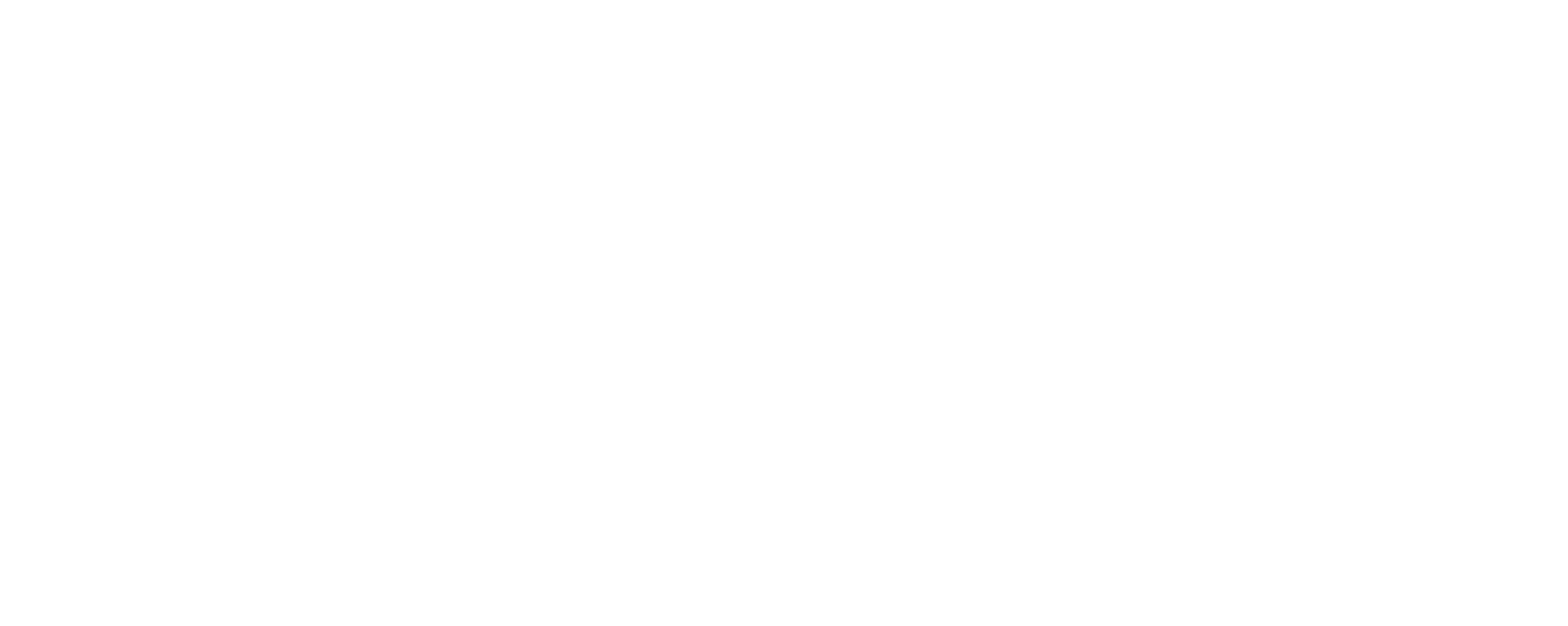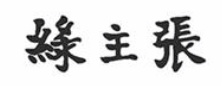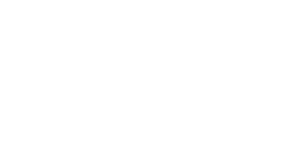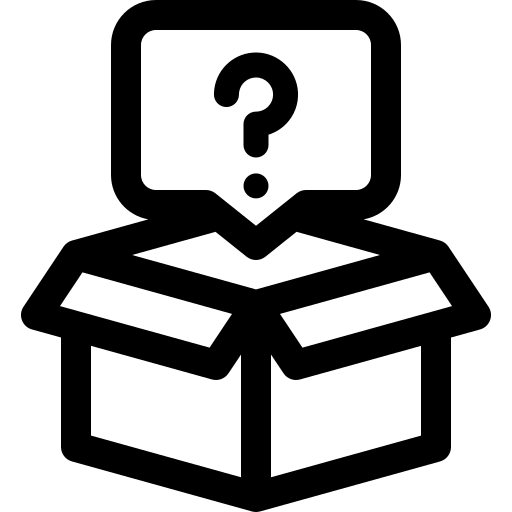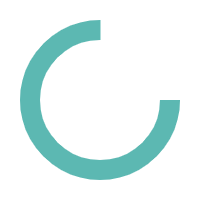小農力量大─國際家庭農業年對於台灣農業的意義
2014-08-07・生活提案
文/吳東傑 圖/朱安棋

▲主婦聯盟合作社的農友翁錦煌嘗試在農場裡架設太陽能板,改善工作環境的溫度,也生產自然安全的綠電。
聯合國訂定二○一四年為家庭農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Family Farming),強調家庭農場對於戰勝貧窮、增加生物多樣性、保護環境的重要與貢獻。然而歐美的家庭農場規模可能達二、三十公頃,台灣的農家生產面積僅約一公頃,是否符合家庭農場的生產規模,必須因地而論。
到底一公頃,也就是相當於約一甲地(一甲等於○‧九七公頃)的農地可以養活一個四人家戶嗎?家庭農場要怎麼定義?在定義家庭農場前,要釐清的是農業的範疇該包括哪些?台灣的農政單位還是傳統的農林漁牧,但因應全球化、都市化、工業化,日本的《農業基本法》在一九九九年標舉為《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德國的農業部則在二○○一年改為「消費者保護暨農糧部」,英國的農業漁糧部也在同年調整成「環境、糧食暨鄉村事務部」。
至於家庭的定義,一個六口、四口、兩口,或是一口人的家庭,則有不同的討論。所以家庭農場的功能也將隨著社會變遷、家庭結構的改變而有不同的功能和定義。
家庭農業,小即是大
縱然有這麼多的不確定性,但是家庭農場的存在及其價值,仍是不可忽視的,甚至需要更多的鼓勵,因為家庭農場將要擔負更多的功能。全球化、商品化的趨勢下,加上都市人口的增加,農業與農產品不再單純;如玉米,可以成為人的食物、畜產的飼料、生質能源的材料,也可以是糖漿的原料。另外,農場也可以種電,農地成為生態、農產與能源的生產基地。
面對強調經濟生產效益的產業鍊,小規模的家庭農場似乎較難找到生存空間;這是以生意的觀點來衡量小農和家庭農場。然而從產業的觀點來看,產業鍊需要更多家庭農場來擔當螺絲釘的角色;而且若考慮到對於生態系統的無上價值,就更需要家庭農場的存在了。反對WTO的南方健將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 曾發表專文支持家庭農場,認為小即是大(Small is big)。向來以大農場經營為政策導向的台灣農業,值得在國際家庭農業年重新省思家庭農場的存在價值。
家庭農場的挑戰
以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小規模確實是家庭農場的缺點,但論及改變與創新的空間,家庭農場則比大規模的農場更具優勢。
台灣是個海島型國家,我們的慣行農業又屬於重藥、重肥,大量使用農藥和肥料,套句台語就是「吃重鹹的農業」。台灣農業也是「進口的農業」,進口糧食就占了七成。如果石油沒了,或是油價高升,我們還吃得起那七成的進口糧食嗎?
台灣目前的能源自給率只有三%,也有人說僅有二%的風力、水力和太陽能;其餘火力發電的煤、化石燃料、核能發電的鈾都須從國外進口,汽車的石油當然也要進口。而糧食自給率是三十二%,但畜牧所需的飼料則約僅有五%是台灣生產,將近九十%的畜牧飼料須要進口。
十年、二十年後,台灣的人口可能減少,但生活方式還是仰賴汽車或化石燃料等產品,包括汽油、農業用的肥料,同時還得進口大量人、畜牧所需的糧食。此外,水資源也愈來愈少,淡水不是早已被污染,就是發生工、農、民生用水相互搶水。
另一方面,極端氣候將對農業帶來衝擊。稻米是台灣的主食,但是稻米的品種愈來愈少,早期的旱稻種植,現在也幾乎完全式微。生物多樣性面臨威脅,物種與品種的消失,剩下愈來愈少的品系,必將難以承受風不調、雨不順的天候考驗。況且面對未來的水資源危機,水稻生產系統也必須調整。
因應未來:社區調適方案
目前全世界約有四、五十個國家、地區從事省水的水稻栽培方式─水稻強化栽培系統(System ofRice Intensification,簡稱SRI)。SRI起源於一九八○年代一位來自馬達加斯加的神父,這是一套在不增加農民額外成本的前提下,增加水稻產量的綜合性方法。
SRI與其他慣行農法的不同之處在於間歇性的供水管理,一般慣行水田的水位較高,但SRI只需二、三公分高的水位,而且以淹水三天、曬乾七天的循環方式,直到幼穗出現(孕穗期)。收割前二十至二十五天開始完全排水,盡可能將土壤的養分轉移到稻穀上,促進水稻根部的發展、增加土壤的通氣性。觀察發現,使用SRI水分管理方法,水稻更為耐旱。
間歇性供水的管理方式使雜草與福壽螺都變少了。種植前兩個月一般會除草三次,第一次開始於移植後的十至十二天,之後每十五天除草一次,一直循環到水稻植株夠大,之後雜草的影響就不大了。在種植過程中,因植株間距大(約二十五公分),於除草的同時還能讓氧氣進入土壤,增加通氣性。因此SRI是相當好的社區調適方案(Community BasedAdaptation,簡稱CBA), 原因無他:因應水資源的短缺,特別是淡水資源。
在地力量:社區支持型農業
另外,什麼是「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Agriculture,簡稱CSA) ? 其推手伊麗莎白.韓德森(Elizabeth Henderson)有一段相當精闢的說明:「堅不可摧的塑膠與石化之牆隔離了現代城市人與食物源頭。尤其是美國,多數人的食物主要來自超級市場、自動販賣機以及速食店裡過度加工、包裝與運輸的食品。很少商店致力於標示食物的來源,加工產品中九成的產值(切割、組配、料理、擠壓、包裝、配送與廣告)淹沒了七至十%自然食材的價值。食物與農民、土地沒有任何連結,而充滿前景、可以改變現狀的另類作法,就是社區支持型農業。」
我們理想中的家庭農場或是農村社區是用SRI生產稻米,以園藝的多樣取代單一種植的單樣,農場還有太陽能和風力發電,社區的家庭人口數則是從一口到多口,年齡層也是從稚齡到人瑞。
在歐洲,小學的午餐來自社區附近的有機農產品,不但能養成學生良好的飲食習慣,還能支持有機農業的發展,而且在地消費是節能減碳的生活方式,亦可改善溫室效應。這樣的農業,不僅是CSA,同時也是一種CBA;而後者的範疇,又增加了前者的功能。社區農業也可以因應特殊族群或在地環境的敏感議題如水源短缺而調整;此時的社區支持型農業可以設計成不需要太多水的灌溉方式,如滴灌,或開發水源,如承接雨水的水撲滿、蓄水池。
家庭農場不僅關心個人的食物安全,同時也希望藉由家庭農場建構社區糧食安全。如何建構健全的社區糧食方案,如公共性的人民食堂(社區食堂、老人食堂)、學校營養午餐等,也是社區支持型農業的重要工作。
社區支持型農業是建立在生產者、消費者,甚至擁有資源者彼此互相支持而形成安全有品質的糧食生產。「支持」的日文語彙是teikei,也就是「提攜」的意思,如何把支持更進一步變成彼此的提攜,不只是社區支持型農業的目的,也是過程。所有人以民主的方式做決策,共同承擔責任,並且在諸如制定價格等決議上,能相互理解或各退一步,這即是民主經濟的建立,也是農民尊嚴與自信的培養。(作者: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