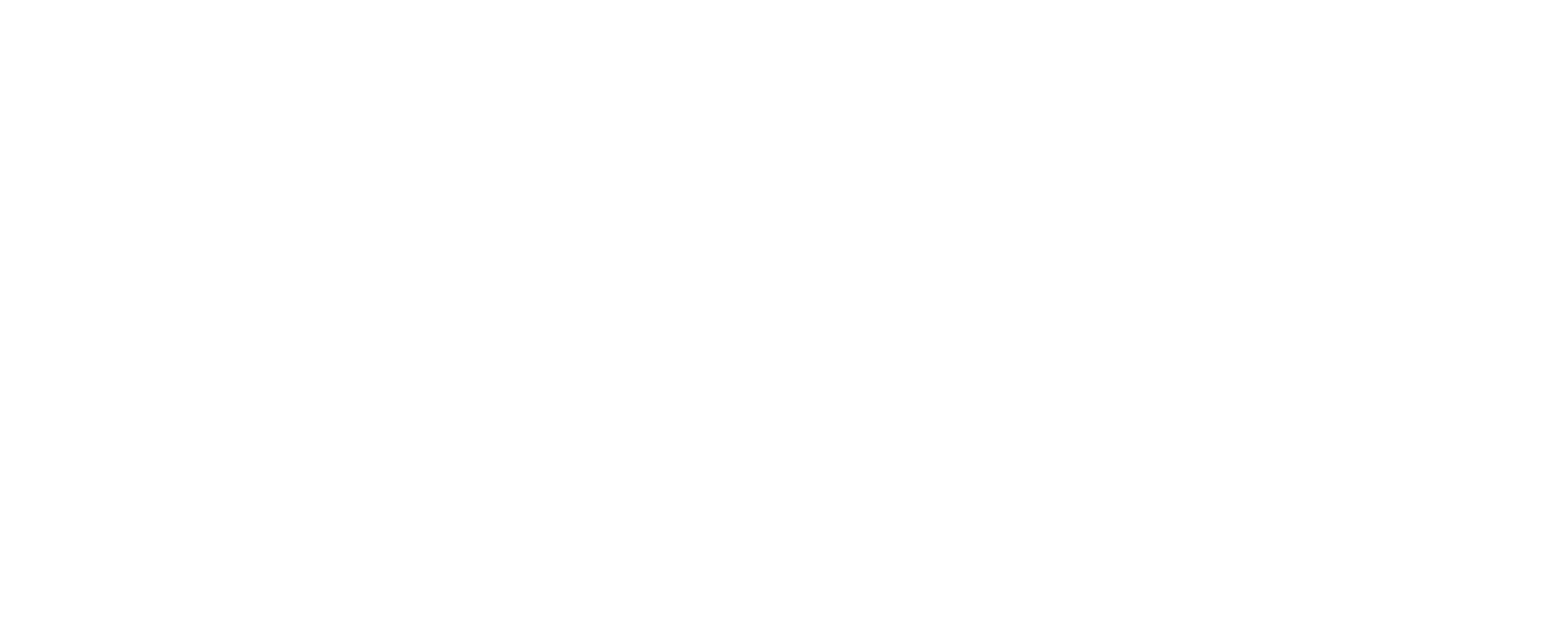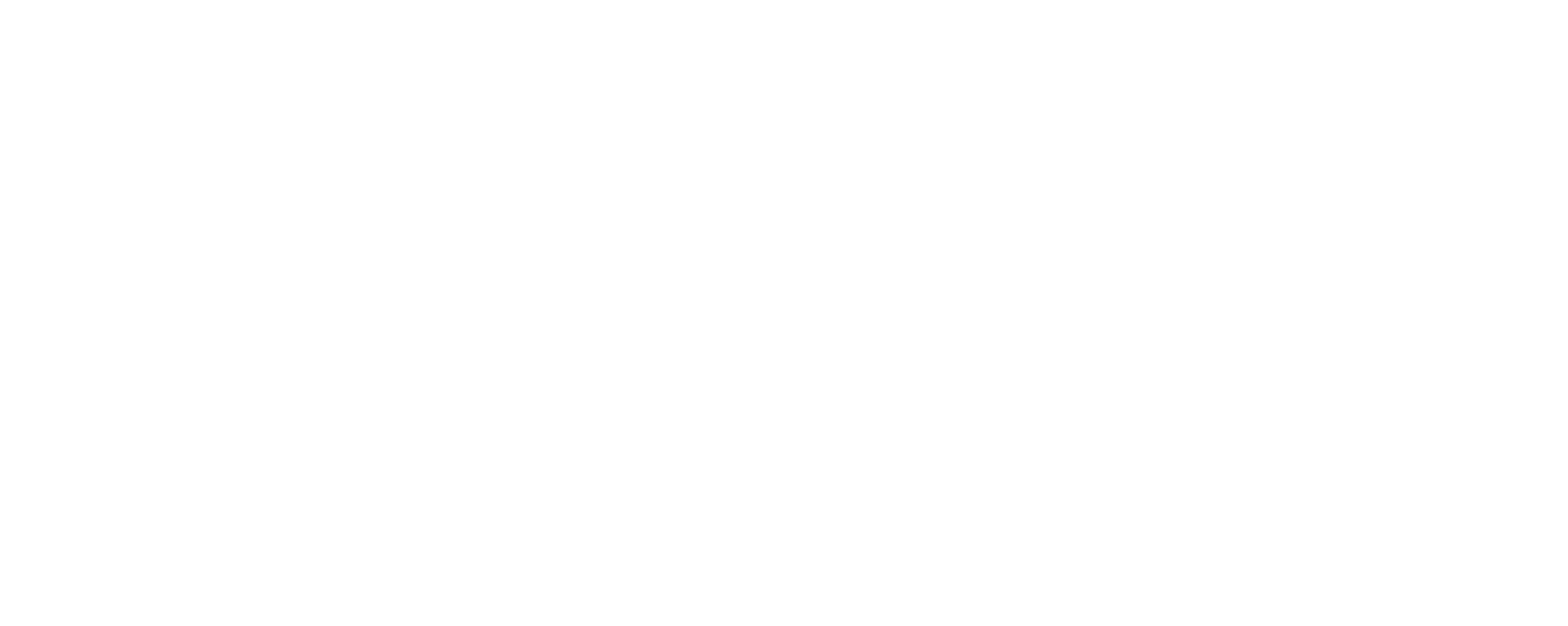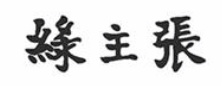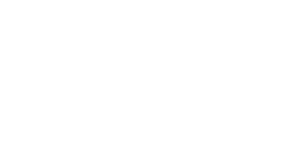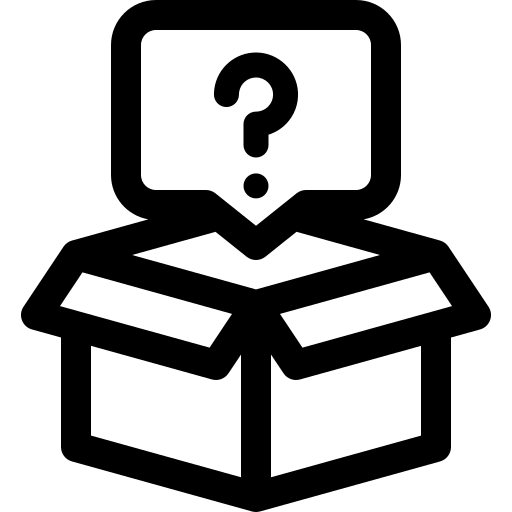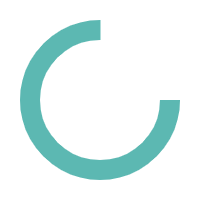從年夜飯想像多元家庭
2014-02-01・生活提案
文.圖/楊佳羚
媽媽在二○一二年十一月過世,正如她所預期的「撐不過年關」。而那年的農曆年,我和先生商量是否能不北上過年,陪伴我爸一起吃第一個一個人的年夜飯。
「在誰家吃年夜飯」:是個性別議題
其實,許多女性婚後就會開始面臨「不能在自己娘家吃年夜飯」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像我這樣的獨生女身上就更為明顯,因為沒有其他的兄弟姊妹能代替我和爸媽一起圍爐。在《大年初一回娘家》及《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我的性別意識成長歷程與實踐》這兩本書中,有朋友分享自己第一年在婆家過年的不習慣與難過;也有朋友分享如何每年輪流到夫家或娘家過年。因為我們二○一○ 年才回台,而竟然是媽媽的過世讓我像「輪流」似的,第一年過年在夫家、第二年在娘家,只是此刻我的娘家裡已經沒有「娘」。
過年是全家團圓、家族聚會的日子,但是我們很少去探問,是哪個「家」在團圓,對不同的人而言,又是什麼樣的意義?還記得當我還單身時,最怕的就是過年,因為親族總不免探問「怎麼還沒有男朋友啊?」、「什麼時候請我們喝喜酒?」, 還讓我因此很想出版《拒婚一百答客問》,以便一一應付不同的催婚狀況。當我開始當國中老師、有經濟能力後,每年都故意選擇在過年期間出國。只是當年年輕,只想逃避親戚的壓力,以為「來日方長」。卻沒有想到能和爸媽圍爐的時刻,從現在算回去,竟然也是倒數的幾次了。

▲海外的年夜飯,充滿台灣人的人情味。
「在誰家吃年夜飯」:是個暮年議題
今年年關將近,要如何過年又成問題。於是我就邀請爸爸,希望他願意到婆家一起圍爐。我猜想到爸爸並不想要,正如許多女性並不那麼習慣在「別人家」過年一樣。然而一方面我以「沒人陪公公喝酒」為由,勸爸爸當公公的酒友之外,另方面可能也因為爸爸想和孫女一起過年,所以就答應了。
在這過程中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想想,晚年時的年夜飯是什麼樣的光景。其實就像我們在國外念書時,因婚姻而移居瑞典的台灣朋友常邀請我們這群台灣留學生共同吃年夜飯一樣,我們在不同的時刻,早已有不一樣的圍爐夥伴。例如我的同志學生的爸媽會在過年時,邀請不能回家過年的同志孩子到他們家一起圍爐;在我晚年時,也會想找女性主義社群的好友一起吃年夜飯;而我們去年在高雄,更意外地與台北下來的朋友一起在大年初二爬柴山反核過年!
別再假裝看不見 生命經驗的多元
上次專欄談了〈多元成家草案〉的第一部分─「婚姻平權」婚姻中立修法,而目前也有各界連署,包括學生、學者、基層教師、法學界、心理工作者、文化界、台灣政治人物、醫學與公衛人士、精神科醫師(註)。然而引起更多社會大眾疑慮的是第三部分的「多人家屬」,讓人以為是不是在多人家屬中會造成「多P」或使「小三」合法化。
其實會有這樣的疑慮, 主要是因為大家難以想像「多元家庭」的樣貌。基本上「多人家屬」有別於婚姻配偶與伴侶,主要是共同居住而產生的「家屬」關係。過去十分知名的美國影集《黃金女郎》,正是房東白蘭琪在喪偶後徵求室友,與蘿絲、一對母女(桃樂蒂及蘇菲亞)同住一屋的故事。這也是典型「多人家屬」
的樣貌。
又例如我所居住的大樓,常可看到兩位比丘尼的身影。最近我發現其中一位已經開始使用助步器,而另一位則常相左右。如果這兩位比丘尼長年來都互相照顧、扶持,來日其中一位若送到加護病房,另一位會因為不具有「家人」的身分,而難以為她做醫療決定。雖然現行醫療法已經讓「關係人」可以簽署相關同意書,但在醫療現場,仍主要只讓具有血緣關係的親屬來簽署;如果關係人和病人親屬有不同意見,也傾向遵從親屬的意見。如果說比丘尼長年來已經少與親屬往來,但最後時刻卻不是這位相伴的比丘尼能為其決定或能陪伴在側,這是否合理?同樣的,由離婚婦女所組成的「天晴協會」姊妹們也分享了一個現實層面的問題,由於台灣的傳統習俗,讓許多離婚婦女不論在前夫家或娘家都沒有位置,不管是生前或死後。若有些失婚姊妹們長期共同居住生活,彼此照顧,卻因為不具有「家人」身分而被許多制度與體系排除在外,又令人情何以堪?
台灣現在雖然只有一夫一妻的異性戀婚姻,但異性戀的「多P」、「小三」仍時有所聞。甚至大企業家的正室、二房、三房子女爭奪財產的消息都登上媒體,也沒人去質疑大企業家犯了重婚罪,或是他的正室為何得容忍他一輩子,究竟出了什麼性別問題?其實要組成「多人家屬」有許多協商過程,不見得有小三的男人都會想要讓小三與太太共處一室;而在這複雜關係中的人們能否經歷這些協商過程共組家庭也是一個難題。
如果我們更能以不同時期、不同身分的生活經驗去設想我們的「老病死生」,也許我們能更明白,〈多元成家法案〉想保障的,無非是這些無法和我們順理成章地圍爐的這一些親愛的家人們。

▲與台北下來的朋友一起在大年初二爬柴山反核過年。
作者介紹
高師大性別教育所助理教授,著有《台灣女生 瑞典樂活》。
備註
婚姻平權各界連署平台整理,詳見伴侶盟網站:http://tapcpr.wordpress.com